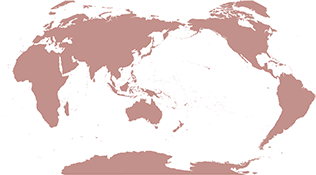
半月谈记者 皮曙初
尊重自然、热爱自然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华文明内在包含着深刻的生态文化基因。长江文明植根于长江流域特殊的自然禀赋与生态环境,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与水相生,与特有的自然生态相伴,其中所蕴含的自然理念与生态智慧,绵延福泽至今。

2019年8月10日,湖北宜昌,洪水经过后的三峡工程全景
远古的记忆:与自然无所违
世界上的古老文明都有着强烈的洪水记忆。中国文明的洪水记忆从女娲补天到大禹治水,无不体现出一种坚韧不屈的奋斗精神和顺天应时的自然理念。
在湖北宜昌三峡大坝下游,有一座高耸陡峭的山崖黄牛崖,崖下有一座黄陵庙,又称黄牛庙,矗立在长江边。庙中供奉的是远古时代治水英雄大禹。大禹持耒傲立,目视滔滔江水。
相传上古时候长江峡谷未开,洪水无路可走以至泛滥成灾,大禹带领群众劈山开河,九载不辍。巫山神女瑶姬有感于大禹的赤诚,命天上的土星化作神牛下凡相助,于是神牛以角触石,撞开巫山,长江自此东流入海。
千百年来,人们不断以各种方式到这里祭祀黄牛,拜谒大禹,彰扬中华民族持之以恒治理长江的英雄业绩,也寄托彻底根除水患的迫切愿望。在庙中保存的《黄牛庙记》碑文中,诸葛亮说:“平治洪水,顺遵其道,呜呼,非神扶助于禹,人力奚能至此耶?”
大禹治水是传说,也是历史。它存在于早期的历史典籍之中,更存在于古往今来华夏儿女的心中。历代广为流传的不只是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精神,还有与其父鲧完全不同的治水理念:鲧集中力量修筑堤防,以期约束水势,但是堤防不能阻遏洪水的冲击,不断地修筑又不断地溃决;而禹总结了鲧的经验教训,采用疏导之法,使诸水各有去路,就其天然的趋势,让小水归入大水,大水东流入海。
大禹治水的故事难以考证其历史真实,然而有关禹治水之功的历史遗迹却遍布各地。在长江沿线,纪念大禹治水的禹王庙、大禹庙就难以计数。故事未必是历史,但是故事中所蕴含的道理,却奠定了中华文明关于自然生态认知的哲学思想。
《周易》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礼记》中说:“凡举事,毋逆天数,必顺其时,慎因其类。”老子则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古代的思想家们,从历史实践中得出了人与自然应该是合拍共存的关系。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远古记忆中留下的哲学命题。季羡林说,“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东方思想的普遍而又基本的表露。
大禹的疏导之法,就是顺天应时,“与自然无所违”。这种朴素的生态思想不仅体现在神话传说中,更体现在长江流域早期的文明实践中。
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就指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因天才,就地利”。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也发现,长江流域早在4000多年前就已经有大量早期城市形态的遗址。这些聚落遗址可谓“择丘陵而处之”“枕山、环水、面屏”“顺天时,量地利”,闪耀着原始的“天人合一”的光芒。
在长江中游,以石家河遗址为中心有16座史前城址,这些城址主要分布于大洪山、荆山、鄂西山地、武陵山向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过渡的接合部,呈现出山水相依的分布格局。比如不久前发掘的城河古城遗址,考古人员研究认为,流经城内的城河并非自然河流,而是经改造后的人工水系,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城内大量人口的用水、排水问题。那时长江中游的居民,已经开始对水系进行利用、管理。
历史的实践:山林非时不升斤斧
都江堰是中国水利工程史上的奇迹。历时2200余年,仍然是集历史文化、科学创造与自然生态于一体,既充满神话色彩、又令人激情澎湃的人文景观。两千多年来,它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如今,它的灌溉面积更是增至1000多万亩。
都江堰为战国时期秦国蜀守李冰始建。李冰采用中流作堰的方法,在岷江峡内用石块砌成石埂,叫都江鱼嘴,把岷江水流一分为二,东边的叫内江,供灌溉渠用水;西边的叫外江,是岷江的正流。又在灌县城附近的岷江南岸筑离碓,离碓的东侧是内江的水口,称宝瓶口,内江自宝瓶口以下进入密布于川西平原之上的灌溉系统。
都江堰的工程效果,便是著名的“分四六,平潦旱”六字诀:每年枯水季节,通过分水鱼嘴及宝瓶口的控制作用,水流自动分成内江六成、外江四成;当洪水来袭,沙洲被淹没,水流不再受河床弯道的制约,主流直奔外江,分水比例变成内江四成、外江六成,以保证成都平原不受洪水袭击。
既不修筑拦断岷江的堰坝,又没有设立控制闸门,却能运用自如地调配水量,使枯水季节有足够的水量进入灌区,洪水季节又能把多余的水量排向外江,使灌区水旱无忧。都江堰如此巧妙的工程布局,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
司马迁《史记·河渠书》记:“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东晋常琚《华阳国志·蜀志》说:“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
都江堰是中国古代治水思想的具体体现,更是长江文明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即便到了今天,水利工程专家们也无不感慨其工程理念,在造福人类的同时并没有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效应,做到了科学、自然与人类利益的完美统一。
古人在实践中已创造诠释了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古人强调:“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
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就有当时农田水利、山林保护方面的法律《田律》。根据对简文的释读,可见当时的法律即有明文规定:春二月时,禁止砍伐山林木材、堵塞河道;不到夏季,禁止焚草作肥,禁止采撷刚发芽的植物,禁止捕杀幼兽、鸟卵,禁止毒杀鱼鳖,禁止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只有到了7月,这些禁令才被解除。
“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历代学者或是朝廷诏令之中,也常有这种不伤生理、不逆时令的劝诫或禁令。
北宋时期的大文豪苏轼,同时也是一位治水的能人。他在《禹之所以通水之法》一文中指出:“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他认为,治水之道不仅要知道“水理”,还要了解“人情”,关键要在“水理”和“人情”之间找到平衡。他说:“河水湍悍,虽亦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势不致如此。”
在任杭州知州时,苏轼带领百姓疏浚西湖,还湖于民。还疏通了杭州城内唐代留下来的“六井”,解决杭州居民饮水问题。为了解决堆积如山的水草和淤泥,苏轼“以水治水”,用这些挖出来的淤泥、水草,在西湖的西侧,修建了一条南起南屏山麓、北到栖霞岭下的长堤。如今,堤上花红柳绿的景色被称为“苏堤春晓”,成为西湖十景之首。
近代的反思:反天时为灾
“天人合一”被许多学者奉为“东方的生态智慧”。但是,季羡林先生早就指出,我们也要看到历史实践中的深刻教训。“我们中国虽然有这种高明正确的哲学思想,但是在行动上我们也没有完全做到,因此我们也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
唐宋以后,对长江中下游的大开发,使长江流域经济发展,新兴城市大量涌现,人口急剧增加,也导致了历史性的后果。
晚清思想家魏源就看到了这一点。他在《湖广水利论》中说,“历代以来,有河患无江患”,长江所经过两岸,“其狭处则有山以夹之,其宽处则有湖以潴之”,所以千百年来溃决很少,不像黄河性悍,横溢溃决无足怪。但是近代以来却不同,长江“告灾不辍,大湖南北,漂田舍、浸城市,请赈缓征无虚岁”,几乎与河防同患。
他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就在于“土满人满”。湖北湖南、江南各省,沿江沿汉沿湖,以前受水之地,筑圩捍水,都围成了田、建起了房,地无遗利。“下游之湖面江面日狭一日,而上游之沙涨日甚一日,夏涨安得不怒?堤垸安得不破?田亩安得不灾?”
明清时期,两湖平原上大量兴建垸堤,一方面带来了“湖广熟,天下足”的农业经济繁荣,另一方面却对荆江、汉江产生巨大影响,两岸天然的分蓄洪区纷纷被筑堤围垦,灾害对经济社会影响随之加剧。乾隆时期,湖北巡抚彭树葵就曾疾呼:“人与水争地为利,水必与人争地为殃。水流壅塞,其害无穷。”
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也关注到这个问题:“近来的水灾为什么是一年多过一年呢?古时候的水灾为什么是很少呢?这个原因,就是由于古代有很多森林,现在人民采伐木料过多,采伐之后,又不行补种,所以森林便很少。许多山岭都是童山,一遇了大雨,山上没有森林来吸收雨水和阻止雨水,山上的水,便马上流到河里去,河水便马上泛涨起来,即成水灾。”
孙中山看到了人类活动导致环境破坏、灾害发生频率及危害程度增加的事实。进入工业社会,对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干预更加激烈,与之相对应,频繁而又广泛的灾害,已成为制约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曾指出,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所以他曾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今天,生态文明是新时代背景下实现人与自然统一、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共赢的新要求。长江经济带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走科学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就是要尊重自然规律,在自然界可承载的范围之内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和改造自然,做到顺天时、量地利,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从而实现“天人合一”的美好夙愿。
这,也是对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半月谈内部版201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