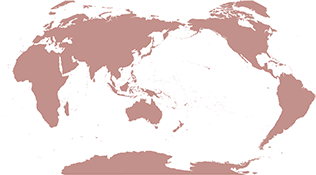
半月谈记者 曾维
作为警察,面对罪犯时他们威严有力;作为医生,面对患者时他们无微不至。本是平凡人,但因肩上的责任,他们坚守在“高墙”内,行走在暴露与感染的“刀锋”边缘。

2020 年11 月21 日,云南建水监狱医院的医护人员正在讨论病情 孙敏/ 摄
云南省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地理位置特殊,因毒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罪犯数量不少。为此,2008年建水监狱成为云南省监狱系统首批试点,设立集中管理、治疗感染艾滋病病毒罪犯的第八监区。
范云富是建水监狱医院的院长,因承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的管理和治疗工作,他和同事们被称为“高墙医生”。
范云富: 和普通的医生一样,我们平时上班也会带着叩诊锤、听诊器、血压仪、手电筒等工具,如果没有穿过的一道道铁门,我们的工作看起来与一般的医生没什么不同。2008年监区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就像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没经验可循、职业暴露风险高,面对全新的任务,不少同事都觉得心里没底。
其实,在到第八监区工作以前,我就经历过职业暴露。2006年,我在为一名长期吸毒的罪犯缝合伤口时不小心刺破手掌,而那天刚巧是我女儿出生的日子。初为人父,我心里既喜悦又觉得很煎熬。那时候心理压力很大,很怕自己被感染了。我瞒着家人服下病毒阻断药物,并在单位进行自我隔离。经历了十多天来自身体和心理的痛苦煎熬,好在2周后检查结果呈阴性。事后,同样身在抗艾一线从事护士工作的妻子才得知这一情况,急得她直掉眼泪。
因为长期坚守在医院工作第一线,同事有事的时候,我一般体谅他们自己顶上。节假日、周末我也经常加班,所以同事们给我取了个外号“范天天”。罪犯经过我们的治疗,不仅身体状况好转,同时也会感受到社会的关心。
如果打个比喻,我觉得我们抗艾医生就像是“灯芯”,用“人道、博爱、奉献”的医者仁心点燃一盏盏心灯,照亮服刑人员的新生之路,重燃他们对生活的炽热渴望。

2020 年11 月21 日,云南建水监狱医院医护人员正在查房 孙敏/ 摄
李文红: 我在监狱医院当医生已经35年了。多年来,我和同事们是战友更是彼此的眼睛,因为工作的特殊性,我们常常同吃同住,在一起的时间比跟家人还要多。
每一个罪犯的背后都有一个家庭。因为对艾滋病不了解和恐惧,“刑期比命长”是这里不少罪犯的心理,自暴自弃、抗拒治疗的事时有发生。2018年,罪犯付某因艾滋病期合并肝硬化导致腹腔积液,情况不乐观。病情一再变重的付某开始拒绝打针、吃药,非常消极。为了使付某配合治疗,我与同事每天上班后都会与他谈心。经过反复劝导和耐心医治,付某的心态有了很大的转变。他觉得医生都很重视自己的病情,自己也该努力。
平日里,这些高墙内的抗艾医生面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心理压力很大。而对于女医生来说,更是面临心理与生活的双重难题。
王锦红: 作为医院为数不多的女医生,我面对的工作压力会更多。考虑到我的安全,从2015年从事这个工作以来,除非是在危重病人紧急的情况下,我一般不单独面对罪犯。
2017年,罪犯潘某因艾滋病发病期引起全血细胞偏低,情况十分危急。得知消息,潘某的妻子带着刚出生的孩子急忙赶往医院,经过我几个小时的抢救,潘某最终还是因呼吸衰竭而死亡。短短一个星期之内,有三位患者相继因并发症去世,而且他们都很年轻。其中有一个病人,星期五下午住院,检查结果还没出来,星期日晚上就突然去世了。那时候,我心理负担很重,社会上的舆论压力很大,病犯的家属也不太理解。
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就那么没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觉得自己心里面过不了这道坎,甚至一度动了调岗的念头,但看到院长和同事们连外伤缝合都会抢着上,我的心里就很感动,最终说服自己坚持了下来。
近年来,这支抗艾队伍仍在不断壮大。作为团队里的90后,松世林的加入为团队增添了新鲜血液。
松世林: 我是2017年加入这支队伍的。刚开始,因工作期间不能用手机我觉得特别不习惯。虽然之前实习的时候去感染科轮过岗,但是一开始面对这些特殊的病人时,心里难免有些紧张。
我跟着老师慢慢学习。门诊治疗、住院病人查房、消毒、预防保健……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已适应自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中,我逐渐意识到,高墙医生要做的不仅仅是治病,还要“治心”,要对罪犯进行系统的心理疏导。这些人既是罪犯也是病人,但是没有亲人在身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更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
2020年3月,我被派到红河州第三人民医院进修学习,“充电”使我对未来的工作更加充满信心。医者仁心,我们尽力救治,在助人的过程中淬炼自己,在互相安慰的过程中不断成长、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