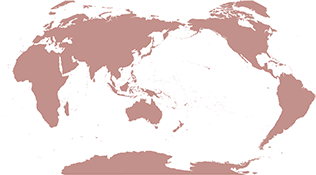
城市,当代人最主要的生活之地。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72%。也就是说,接近2/3的人聚集在城市。城市,不仅是经济产出之地,也应成为美好生活之地、精神寄托之地。然而,现实并不总是如意。许多人不时念叨着“乡愁”,憧憬着“诗与远方”,对于此时此地所居所在的城市,似乎总是少了一份归属感。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艳玲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中,人们为了更美好的生活而奔向城市,但城市往往成为压力与疏离的代名词,城市中的人们时常经历着“回不去的乡,融不入的城”的双重拉扯。人们之所以怀恋乡村生活,本质上是因为城市生活的不如意,也即“乡愁本质上是城伤”。
那么,城伤如何疗治?何艳玲新著《人民城市之路》提供了一个极富中国特色、兼具实践性与理论性的回答。就此,半月谈记者对何艳玲进行了专访。
城市的特质和治理的本质
半月谈记者:“人民城市”这一说法似乎早已有之。在《人民城市之路》一书中,您对“人民城市”这一概念赋予了怎样的不一样的内涵?
何艳玲:“人民城市”的说法虽然久远,但其内涵并不十分明确和充实。本书所说“人民城市”,从本质上理解,是指在制度化城市权利的基础上,实现人民在城市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城市,作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一个物理场地、经济场所、社会场景,其集聚性、规模性和流动性,让制度变得更为复杂,不确定性增强,风险性加大,伤害也变得更有可能。因此,指向人民城市价值导向的城市善治越来越迫切和重要。
新时代,中央重视城市人民性,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在城市治理领域的深入落实,也指引了人民城市建设的未来。城市人民性涵盖城市发展属于谁、依靠谁和为了谁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阐明了城市的性质问题,即人民是城市的主人,城市是属于人民的,人民性是社会主义城市的根本属性;其次,人民创造了城市,城市建设和发展必须集中民智,汇聚民力,依靠人民的奋斗和拼搏,尤其是要将人民吸纳到城市治理的各个环节中来,共同管理好城市家园;最后,城市的进步和发展最终都是为了人民福祉,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简单说就是,城市归人民所共有,由人民共同治理,最终实现人民共享。
半月谈记者:您在书中提到,“乡愁本质上是城伤”,为什么这样说?当下我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及其根源是什么?
何艳玲:长久以来,在增长主义的逻辑下,城市的首要目的是获得经济上的繁荣与发展。城市空间被看作生产和工作场所,而非生活和交往的场所;土地成为商品,而非栖居的载体;流动人口被看作劳动力,而非居民。人们在城市中的行事以标准化、理性化、去情感化为导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对温馨感情的向往反而被视作与增长无关的“多余动作”。这造成城市与人之间的疏离。
同时,城市特有的集聚性、流动性和异质性所带来的城市与人民的疏离,让城市治理变得更艰难和复杂。其中,集聚性是城市最重要的特质,但高密度聚集的人口也带来交通拥挤、住房拥挤、垃圾围城等难题;流动性加剧了城市的陌生化和原子化,弱化了城市居民间的认同与信任,更消解了城市居民自主解决问题的社会资本;异质性带来差异、分歧和利益、价值观的不一致,也成为城市冲突的重要来源。
如果城市不能提供一种精神上的家园感,人们就会把这种情感寄托在别的地方,比如回不去的故乡、理想化的远方,乡愁由此愈加挥之不去。
半月谈记者:如此说来,“人民城市之路”也应从这些方面着力?
何艳玲:是的。在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必须更加强调从城市居民生活需求的角度,来思考和应对复杂的城市问题。城市作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与人民的汇聚之地,既是增长的火车头,也是治理的最大载体。不同于乡村治理,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的治理,本质就是管理好集聚性、异质性和流动性。
理想的“人民城市”须兼具活力、宜居、可持续这三大特质。其一,城市活力最直观呈现为经济活力,严格来说就是来自于人的创新创造的活力。其二,宜居作为一种主观体验感,其基本源泉是人民获得感,其实现依赖于城市的便利通达和舒适的场景体验。宜居是城市质量的最高体现和生动写照。其三,可持续是发展的需要,是和谐的支撑,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保障,城市必须实现三个层次的协调: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协调,供给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深度融合。

依托社区进行精细化治理
半月谈记者:在城市治理中,您提出要“靠近人民所在的社区实现精细化治理”。为什么把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和切入口?
何艳玲:从以人为中心的角度来看,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的尺度是社区。在复杂的城市系统中,社区是一个敏感单元,是人民直接可感知的空间,能反映人民实际需求,传达人民真实声音。为此,精准高效的城市治理必定会聚焦在社区这一居民生存生活的共同体,必定会着眼于社区这一人群聚集的最小敏感单元,必定会聚焦于每个独具个性的社区居民,将发展和治理建立在可感知的空间的基础上,从人民身边的改造做起,从人民肉眼可见的变化开始,让人民对城市发展和政府的努力看得见、摸得着。
在中国体制和语境之中,社区同时承载着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管理属性,是适度的土地和空间,人民之间交往与互动的合适载体,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的“最后一公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活观念的转变,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愈发强烈,呈现出个性化、多样化与差异化的特征。在这种背景下,精细化治理是最好的回应方式,社区则是城市精细化治理最适宜的治理空间。
半月谈记者:如您所言,社区治理确实应成为城市治理的基石。不过,当前不少城市社区似乎还难以承担这样的角色和任务。它们普遍的困境是什么?出路又在哪里?
何艳玲:党的十八大以来,社区治理被提升至执政战略的高度。要将社会治理的重心落在城乡社区,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的“最后一公里”。社区治理的空前升格有其现实关切——改革开放40余年来,在市场化的席卷之下,人口流动性、个人原子化、身份异质性、利益多元化带来的社会碎片化,封闭社区象征的空间碎片化,社区场域内居委会、物业与业委会各行其是和政府内部相关部门条块分割共同导致的权力碎片化,以及党组织的悬浮化等种种因素造成了社区的低组织化和治理内卷化。在横向联结疏离、纵向整合失序的治理体系中,社区陷入自下而上的居民诉求得不到有效回应,自上而下的政策政令难以落到实处的困境。
总之,城市社区是复杂的,按照人的需求、感受、适宜尺度以及社会关系来组织、建设和治理,注重邻里交往和场所感,是应对这种困境的关键。
至于具体出路,我觉得成都的探索,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启发。首先,成都设立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首次在党委组织体系中确定一个综合部门承担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政治责任,将社区治理上升至全新的战略高度;其次,建立政党统领、联动协同为上下同构的核心治理机制,设计规范化、稳定化、整合性的政策体系保证治理行动的主动化、常态化和制度化;再次,将精细化治理向末梢延展,特别是在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下,激活居民公共参与,创制小区自治组织,搭建协商议事平台,实现有组织、有秩序、有效能的院落自治;同时,讲求人本逻辑下发展与生活高度融合,在新技术助力下将小尺度、微治理、差异化的治理思路尽量落实。总之,我认为,成都在党委统筹下面向人民的社区精细化治理,蕴含着城市思维与人民思维的回归,为解决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困境提供了样本。
用中国实践重构治理理论
半月谈记者:本书的一大亮点,是基于中国实践来进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建构,尤其是,对党的领导为何必要、作用如何发挥等论述十分深刻。那么在中国的城市治理、社区治理中,如何理解党的作用?
何艳玲:研究中国课题,不仅要吸收借鉴西方的理论,更要从现实出发,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国的最大现实,就是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核心领导作用,必须以政党的全新角色重构治理理论。
具体到城市治理、社区治理,党组织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具有两大任务属性,一是领导核心,即政治属性;二是代表人民,即治理属性。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属性和治理属性相结合,表明党的领导和治理在实践中密切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过去,党与具体治理工作的结合并不充分,党和人民联系的“最后一公里”不够顺畅,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也不太充分。这些都是新时代必须回应和解决的问题。地方治理实践表明,党组织的双重任务属性,可以在具体治理过程中相辅相成,在保证政治方向的同时让党组织具体嵌入治理过程中,并完成各种创新和治理任务。双重任务属性,也意味着在城市治理实践中,党组织的运作将以解决和回应特定的治理问题为导向,不仅通过自上而下的组织建设将权力延伸至各个领域,而且为不同社会群体提供了传递诉求的制度化通道,从而与行政体系共同回应复杂化的治理需求,并为我们理解中国场景下党与人民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
半月谈记者:您在书中多次提到,只有基层党建做好了,社区治理才能做好。为什么这样说?基层党建的主要内容和指向应该是什么?
何艳玲:随着社会的高速转型与社会流动性的加剧,传统组织化路径发生一定程度的断裂:一是部分社会成员与政府的联系不再畅通,成为公共组织之外的孤立个体;二是个体之间的组织化联系中断,劳动力高度流动令社会联络减弱,个体逐渐原子化。个体的原子化又进一步加剧了个体与公共组织的距离,个体不具备足够的私人关系和能力来解决面临的问题。在组织化薄弱的情况下,党组织理所当然地成为再组织的载体。较之于以任务效率为导向的行政组织,党组织有更易伸展的空间,从而可以借助组织网络在基层的延伸不断吸纳和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在社会不成熟的条件下发挥“以党建促进社会建设,以政治整合促进社会整合的作用”。
由此观之,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实质是:党组织在社会发育滞后、联结机制断裂和社会行动能力不足的松散型制度环境中,通过内生性的体制力量激活社会,并以此增强体制回应复杂问题的韧性。
沿着这一逻辑,我认为,基层党建主要应做以下工作:一是在松散社会下建立治理网络。在松散社会形态中,党承载着建立、激活和管理网络的核心角色,依靠自身的强大合法性,通过再造党群服务中心等组织载体,重新扎根群众;发挥网络枢纽的制度功能,将脱嵌于组织的原子化个人组织化,将零散的市场、社会各个主体织在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网络中。二是在立体化网络结构中实现有效治理。一方面,要培育造血能力强且坚守社会公益的治理力量;另一方面,更要以制度化的共建机制统一调动党建网格中的多元力量、多样资源,整合优势社会资源互惠互利,激发协同效应的治理效能。
半月谈记者:本书是基于成都实践写成的。总体来看,成都实践对其他地方和全国的启示性意义何在?
何艳玲:总的来说,成都的实践经验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城市治理专业化的基本路径,揭示了成都对于“何为人民城市”的构想以及“如何建设人民城市”的思路、方向。其基本路径包括:将城市治理作为以人民为中心治理的轴心,将社区作为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主场景,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与高品质生活在城市有机融合以及城市治理嵌入空间视角。二是城市治理专业化的实现机制,呈现了成都“如何实现人民城市”的机制和策略,以及政党、政府、市场、社会等不同主体在参与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其实现机制体现为:政党高位推动、统领全局治理,基层党建引领、构建共治合力,建设学习型政府,持续制度化创新,联结人民,社会增能。
在根本上,成都建设人民城市的实践进一步回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统一体制是如何保持活力的?我认为,成都大城治理的系统创新之所以能实现,其底层逻辑是整体领导的共识治理,这是中国故事如何突破统一与活力之间的张力的理论底色。整体领导的共识治理基于统一与活力的人民性意涵统一起来,在使命型政党的领导下,政府、人民、市场、社会所有要素形成了广泛的共识,政治引领、制度规范、专业技术、市场机制和社会资本等多种逻辑围绕着回应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频共振,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相对统一。这也是成都实践对其他地方和全国的启示性意义所在。
来源:半月谈
半月谈记者:高远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