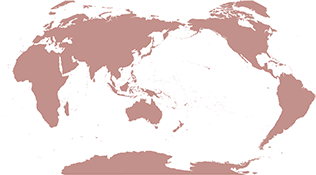

漫画 :多国限制农产品出口(图片来源 :人民视觉)
王亚琪
人类正进入充满风险的失序时代。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至2022年,全球经济将累计损失约13万亿美元的收入;发展中国家将有近3亿人面临粮食安全问题;疫情制约全球经济复苏,增加了多国债务与就业的脆弱性,进而破坏社会稳定。全球事务中的多风险联动,凸显全球治理体系的内在缺陷,加剧世界秩序的转型困境,促使变动和不确定性成为国际社会常态。如何认识全球多风险联动积聚的内在逻辑,探索消减全球治理不确定性的合理路径,成为当今世界政治的一大挑战。
风险之源:现代化、全球化内嵌的“副作用”
在传统社会,台风、地震、洪水等自然风险左右着人类命运。以地理大发现为开端,随着西方文明主导下的现代化进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风险的实质悄然转变。客观存在于物质环境中的“外部风险”被“人为风险”取代,成为现代社会风险的主要来源。
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发展,传染病、核污染的影响跨越洲际,造成的生态危害波及数代人;大气环流和水循环成为污染扩散的载体,地震海啸伴随核泄漏造成复合灾害;转基因作物和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类健康的长期影响至今无法确认。
为了管控风险,人类社会不断推进技术手段的进步,并在现代化进程中建立了一系列制度机制,促使现代社会的组织和运行体系日益成熟和复杂。比如:全球金融体系既服务于资金融通,也可能成为制造资本投机和金融风险的场所;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经常成为成员国制造贸易摩擦的手段;世界卫生组织本该在疫情防控中发挥治理核心平台的作用,却成为部分国家推卸治理责任的受害者,公信力和权威受到挑战。风险出现时,看似诸多行为体和机构皆在确认和管理风险,但实质上没有一个行为体或机构能明确地确定风险根源并承担责任。
于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生态和技术领域的风险首先出现,导致各国围绕稀缺资源展开激烈争夺,继而加剧全球发展分配的不平衡、制造新的国内和国际不平等,最终引发各国在风险应对方案和责任分配上的博弈和冲突,产生全球社会和政治风险。现代化指向时间,全球化指向空间,在两者共同作用下,各领域的不确定性跨越时空交织集聚,新的风险与控制风险活动交织伴生,全球风险社会由此生成。
失序之因:西方中心治理体系衰朽
全球风险社会中,资本在全球范围逐利,污染物和病毒跨越国界流动,风险在多领域间联动积聚,风险管控主要依靠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主导该体系的规则治理理念,以工具理性为基础,与西方现代性思维密切相关。它始终试图在全球风险产生的原因及结果、治理的目标及其手段之间寻求清晰的线性关系,将治理实践中产生的不确定性视为“异常”,认为只要提高信息收集和分析技术,创设足够精密的利益协调机制,就能构建“完全理性”的治理体系,彻底避免不确定性。
由此,西方世界主导构建的现存全球治理体系显示出鲜明的二元对立思维,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人类与自然、东方与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视为二元对立结构,并认为二者间必有一方应当处于优势地位,进而在双方的矛盾冲突之上建立“理性”的契约和机制安排,实现有效治理。
但事实上,面对全球风险,以领土划限、从本国利益出发的主权国家难以避免对各类治理机制的工具性立场,势必将全球问题的界定和应对视为可基于成本收益分析选择的政策目标,将“理性”设计的治理机制异化为维护私利和转嫁治理成本的手段。
西方大国在人类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长期掌握主导权,习惯于将自身的发展模式作为唯一正确的现代化路径,将非西方国家视为需要加以引导和规范的“治理对象”。在实力稳固时,它们定义风险来源,根据自身发展水平设置治理目标,依照自身利益需要规定治理议程。当实力相对衰落时,它们又倾向于凭借在既有制度中的优势地位,推卸治理责任、“修正”治理规则,由此导致全球治理进程低效甚至倒退。
概言之,受领土主权限制的国家行为体与不受领土限制的全球风险间的结构性矛盾,是现存全球治理体系合法性和行动力衰朽、被主权国家作为利益博弈工具和责任推诿手段的根本原因。
西方大国在全球风险界定和治理责任分配中不合理的优势地位,及其在国际权力转移背景下对自身道路、制度、文化优越感丧失的忧虑,已经成为全球治理不确定性生成的重要根源。
如果发达国家继续将发展中国家各方面的落后视为风险的根源以及相对收益的来源,势必加剧全球不均衡发展和全球治理体系中领导力和行动力的匮乏。

印度孟买居民接种新冠疫苗(图片来源 :人民视觉)
应对之道:全球共同风险下的命运共同体
当前,围绕世界体系转型与全球治理变革的争论,不仅是基于理性选择的利益之争,更是关涉价值判断的理念之争。
全球多风险联动的现状表明,现行基于工具理性的规则治理理念,已全面落后于全球风险时代的治理需求。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保守内顾化转向,揭示了西方现代化道路及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合法性和有效性的衰朽。
全球风险已经成为各国必须平等面对的共同命运,它要求我们接受差异和多样化,尊重不同文明、不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和治理理念。正如德国风险社会理论家乌尔里希·贝克所指出的:“要从政治层面应对全球共同风险,就必须形成全球范围的共同努力——共同命运所组成的共同体。”
要消减全球治理不确定性,需要首先重塑国家在全球风险管控中的角色定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止是一种人文关怀,更是基于各国的共同生存利益。一方面,国家需要以全球利益与本国利益的兼容性为行动基点,基于权责一致的原则,合理参与各领域治理机制、承担治理成本。另一方面,国家需要突破传统的疆界和主权观念、重新定义和组织自身的权力和治理资源,依靠与他国的协调合作、与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事务场合中的有效配合,以及对治理规则和机制的遵守和运用,增强全球空间内的行动力和影响力。
在全球风险时代,新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关键,在于将各类治理主体视为共同面对风险的“社会人”,而非具有相似理性的“经济人”。各国应将全球治理塑造成共同参与的认同重塑过程,将“他者”视为相异却又完全平等的互助伙伴;不再强加单一的治理规则与标准,而应在重视人类利益整体性、开放多元、平等正义和共同发展等价值理性的基础上,充分认识不同国家在风险的历史责任和治理能力上的差异;引导各国开展务实的治理合作,促使全球治理体系向着容纳多元文明、尊重多样治理理念和实践、谋求共同发展繁荣的包容型治理体系转变。(作者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