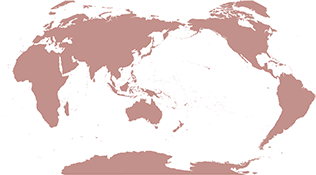
肖阳明
大姨,是母亲的三姐。只因从未见过其他几个姨,所以一直喊三姨叫“大姨”。
从我记事儿起,我就是跟着大姨生活的。直到该上学了,这才不情不愿地离开大姨,不由自主地回到那个“陌生”的家。
大姨的家离县城不远。出家门,下个大坡儿,过条小河儿,沿着新修的铁路边儿,徒步到县城也不到半个点儿的时间。有人问起来,村里人常说:俺是城边儿“南岗头”的。其实,县城本就不大,东边隔条枯河(季节河),对岸就是韩王山,山脚下横亘着一个大岗子,自北向南排开的是三个带“岗”字的村庄。与其相比,感觉“家”很遥远,不仅要从县城坐火车,先到一个叫“偏店”的地方,还要翻山越岭再走老远老远的路。
大姨的家不但破旧,而且很小很暗。房子只有小三间,还是那种低矮的土坯房,除了房顶盖着的瓦片勉强中看,屋内的空间则小得可怜。一个土炕,加上一个标配的煤火台,已经占去大半个空间,再刨去几件破旧的家具占地,屋内就只够几个人转圈了。好在大表姐出嫁了,大表哥陪奶奶另居它处,只有我跟大姨、姨父还有一个长我几岁的小表姐同住。
跟当地多数农村一样,大姨的房子起架不高、窗户很小。本就不大的窗户,只在窗棂的中间安装了一小块儿玻璃,玻璃的四周全部糊上了麻纸。如此这般,其采光的效果也就不难想象了。好在院子足够大,玩伴儿足够多。
院子北边,正中一个大门,门内两家院子相连,中间没有任何阻隔,仿佛一个大家庭,实则住着两家人。同院的那家主人姓冯,与大姨家的贫农身份不同,冯家出身富农。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冯家难免遭到一些排挤,疏于与人交际。受此影响,两家大人之间很少交流和沟通。
孩子们不懂大人的世界,相互间的玩闹依然不少,加上邻家背舍孩子们的穿动,自然断不了一起玩闹,而且玩得很好。在我记忆中,除了雨天或其他特殊天气,我的欢乐时光多是在院里或街上、与玩伴儿们一起度过的。固然,这一切都不能逃离大姨的视线。
那时的大姨,中等身材,常穿一件自制的立领大襟上衣,或青或蓝,一贯的素色;略带花白的头发,总是被收拾得很好看,从不凌乱;圆润的脸上,时常透着笑容,时不时还会发出爽朗的笑声;除了那双缠裹不够到位的小脚,身体还算壮实,两手粗糙而红润。总体上一看,她就是一位乐观自信、干净利索、手脚不停、善于操持家务的人。
大姨对我,看得很紧,唯恐有啥闪失。我不止一次地听她跟我讲,你曾有个哥哥叫“铁如”,属狗,大你五岁,长得长方脸、大眼睛,白白净净,非常懂事。他也是跟着大姨长大,五六岁才回“家”。期间,曾偶遇一个算命先生,大姨让人给他算个命。不料,“先生”一番问话后却说:“这孩子身无疤、疮、痣点,恐难成人!”大姨听后,拉着铁如悻悻离去。谁知一语成谶,铁如回“家”后,竟因急性脑膜炎不治而终。受此打击,母亲一蹶不振,身体骤然垮塌。可怜我还是个一岁多点儿的孩子,大姨决意把我带走抚养。
对于儿时的事情,大多没有印象了。唯有吃,成为我不可忘却的记忆。关于吃,老家涉县有一句俗话:“三天不吃糠,肚里没主张”。这句话,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态。大姨家也不例外,同样没有摆脱“糠菜半年粮”的窘况。即使这样,在大姨眼里,这都不是事。“大人咋都行,小眼儿不行”。这句话,几乎成了大姨的口边话。
“小眼儿”是我无数小名中的一个。据说,小孩儿多几个小名好,名字难听点儿更好成人。大姨家这样叫我,村里的邻居和玩伴儿也都跟着这样称呼我。直到我长大成人以至退休后去到村里,童年的玩伴儿看见我,仍会热情的打招呼:“小眼儿回来了!”儿时的我,很瘦小,体质也很弱,常常闹病,一病就高烧,害得大姨没少担惊受吓。
食物少没啥,紧着孩子吃;挑食也不怕,换着花样吃。为了能让我吃饱吃好,对我挑食的毛病,大姨可是费尽了脑筋,没少给我开小灶。窝头不好吃,她就把窝头做成“窝漏”(漏斗状),里面塞个软柿子;山药、红薯吃腻了,她就和点儿杂面,用鏊子摊成煎饼;偶尔伤风感冒了,那就拿稀有的白面伺候,做成揪片儿、面叶儿或拌面疙瘩儿,最后还不忘拿出一个盛着香油的小瓶子,再拿筷子进去蘸蘸、往碗里甩上几滴。一番操作之后,那是真叫一个香啊!要是碰上红白喜事,抑或走亲串戚、逢年过节,但凡有点儿什么好吃的,总会留出一点儿,将其装到篮子里,再用一个木勾子将其挂到房梁上。谁都别想惦记——那是小眼儿的独食儿。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忽然有一天,大姨黯然神伤的对我说:“你七岁了,该回家上学了!”话没说完,已是泪眼婆娑。而我却懵懵懂懂,不知大姨为什么要哭。临走前的几天,大姨一直不大说话,只是一个劲的缝洗、整理我的衣物,恨不得把所有好吃的都做给我吃。
父亲从县城来接我的那天,大姨的情绪稍微好了一些,但仍然唠叨个不停:“放假就好了!放假就好了!放假就能见到大姨了!”听起来是在安慰我,不如说在叮嘱我。临走前,大姨将一个无数遍打开又包好的包袱,郑重地交到父亲手上,仿佛在交接一项重大的使命。
送出大门,大姨不肯止步。她拉着我的手,身体紧紧地贴着我,迈着“小脚”,踩着高高低低的的石头路,一言不发的向前摇摆着。走到村口高台处,转脸儿就是一个长驱直下的陡坡,再无任何视线阻隔,这才停下脚步。大姨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又不知说啥好,嗫嚅间已是泪流满面……。在大姨的目送下,我五步一转身、十步一回头,依依不舍地走开了,大姨则站在原地、眼睁睁地望着我,直到视线里的身影逐渐的模糊、消失。
直至今天,那个别离的场景,依然像电影里的画面一样,清晰地在我脑海里一遍遍播放。上学后的头几年里,每到麦假、秋假和寒假,我就像只放飞的小鸟一样,迫不及待地来到大姨身边。
每一次的到来,都是那么的兴奋;每一次的离别,都在重复着不变的场景。直到五年后,那个小我一轮的妹妹去到大姨身边,顶替了我在大姨心中的位置。小妹是大姨为我们家抚养的第三个孩子。
每每讲到大姨,父母都会无限感慨地说:“大姨是咱们家的大恩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你们大姨!”据母亲讲,大姨一生没有生育。因为喜欢孩子,大姨相继抱养了大表姐、大表哥。三舅家原本有个闺女,想再要个儿子,没想到又生一个“丫头片子”,大姨说句“我要”就抱走了。
大姨没有一个亲生骨肉,却实实在在养育了六条生命。从嗷嗷待哺到蹒跚学步,一口口喂养,一个个成人。那是怎样一个过程啊,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她是怎么熬过这成千上万个日夜的,又是什么信念在背后支撑着她!
斯人已去,我该问谁呢?!
大姨!我想您!